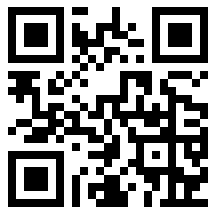“电影是门语言,想法来自导演,答案握在观众手里。”伊莎贝尔·于佩尔对一群未来电影人说。转身在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她关于戏剧的表述异曲同工:“在舞台上,我是导演的容器,承载他的思想,表达他的意愿。”
在法国国宝级女演员的认知里,电影和戏剧本质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一门与人交流、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语言。演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同跨语言交流的“转译者”。至于对话效果,取决于表达者、聆听者、转译者的合成,缺一不可。某种意义上,于佩尔的这次上海行,既是中法文化在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的碰撞,又何尝不是国际交流中彼此消弭“文化折损”的双向奔赴。
12日下午,于佩尔现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在与学院特聘教授、威尼斯电影节前主席马可·穆勒的对谈中,分享她的“艺趣人生”。当晚,她化身“柳鲍芙”,将《樱桃园》的时代记忆带到上海文化广场舞台。

牛仔裤、运动鞋,几乎全素颜。两获戛纳电影节影后,两获威尼斯电影节影后,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熊奖⋯⋯于佩尔的松弛感来自其无与伦比的艺术生涯。第四次到沪的她毫不掩饰对上海的喜爱:“上海的能量和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以戏剧现场为例,认为边看字幕边观剧是种极易疲倦的体验,“上海观众竟然可以那么专注且认真,在他们的掌声里,我可以听到澎湃的热情”——此刻的互相聆听,是成功的。
把百分百信任交给导演
马可·穆勒在介绍于佩尔时,用了一连串量化表达:她职业生涯出演过120余部影视作品,囊括欧美各大电影节最高荣誉;她合作过的导演遍布全球,从法国、瑞士、美国、荷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的作者到韩国、菲律宾、柬埔寨等亚洲国家导演,都曾把镜头对准于佩尔。大师级的如戈达尔、哈内克有之,以个人处女作发来邀约的亦有。
是什么给了于佩尔滋养,让她能跨越国别、语言、资历、生活环境等因素,与不同班底合作?

于佩尔给出关键词“信任”,“表演是建立在导演与演员互信关系上的展现”。如果不是保罗·范霍文,她可能不会出演《她》;如果不是哈内克,就不会有《钢琴教师》里的她,“表演有时也是冒险,有了信任,演员才会大胆尝试”。而对于新锐导演,于佩尔觉得,与其在内心衡量导演是否过于年轻,不如“忘记”这是他们的处女作。作为一名更有资历的演员,“如果与导演之间产生所谓权利的驾驭、制衡,恐怕拍摄中会有堵滞”。
在戏剧舞台,触发她第一记心动的要素依然是“值得信任的合作者。”于佩尔坦言,自己挑选作品的标准非常简单——“看导演”,无论是《玻璃动物园》的伊沃·凡·霍夫,还是《樱桃园》的蒂亚戈·罗德里格斯,每一位杰出导演都在激发着她的创作热情。
把百分百信任交给导演,“这样可以让我更轻松、更纯粹地投入表演中,而不必产生飘忽不定的想法。”于佩尔说:“这么说或许有些冒犯地——有些演员过于强调表达自我,反而会抢戏。一位好导演不会生硬地强迫演员,他会和我们一同踏上旅程,去探寻表演的真谛。”近期,于佩尔还与导演罗伯特·威尔逊合作了一部独角戏《玛丽说了她说的话》,剧中有大段独白,“演起来非常过瘾,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部戏带到中国”。
许多问题其实是世界普遍的
“法国有个短语,‘杯子里有半杯水’,消极者认为有半杯水已经被喝掉了,积极的人会想,不错,还有半杯。”于佩尔的法语翻译边转述这句话,席下不少人已心领神会。表达乐观与悲观情绪,语言不同,但我们理解一致。

相似的情况还体现在“听”与“听见”“人”与“人物”“影迷”与“迷影”等细微差异。有人求解音乐能否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于佩尔的个人偏好是“听”一下,但并不一定要“听见”,“想象力应该如同白纸般纯洁,而不是非得受到其他元素的影响才能被点燃”。演员投入表演再外化到镜头前、舞台上的表现,是她自己抑或不是?于佩尔说:“她是我也不是我,她更像是我戴上面具去诠释的人。”她借法国导演雅克·杜瓦荣的观点说,“演员不是演人物,而是演人”,人物或许会被限定在具体的言行举止范式里,但人性是普遍的,“演员要演人,不要演某个人物的具象化行为”。

今天,电影和戏剧这两门艺术的生存生态成了跨国别的话题。对此,于佩尔的回答富有时间沉淀的哲理性。“最近巴黎有个书展,法国媒体报道说年轻人正在远离阅读。我想电影或者戏剧可能先行一步,已经度过了书籍当下的波折处境。”她说,电影最难的时候,法国电影也会为争取更多票房的商业性与主张艺术表达的文艺片而困惑。好在,至暗时刻已经过去。
“全世界都有相似的故事,好电影未必有高票房。”于佩尔说,重要的是,我们比以往能更多地彼此看见。她的大儿子洛伦佐,与父亲一同接手了巴黎一家老牌院线的经营权,“那里曾经都是老式的美国影片,他们负责经营后丰富了排片。现在有墨西哥电影、亚洲电影,让巴黎的迷影人群有机会看到全世界不同的影片”。
“我打小就喜欢看戏看电影,从中探寻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已经深深刻印在了我的生命里。好的艺术作品仿佛一块美味蛋糕,永远能勾起去咬一口的冲动。”于佩尔说,对世界的彼此了解,始终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在她眼中,中国有许多才华横溢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娄烨的作品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则有着震荡人心的力量。“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值得被更多人‘被看见’。”于佩尔说,自己还注意到毕赣导演,“他的作品蕴含着灵性的诗意,导演还那么年轻,我非常看好毕赣的未来,期待有机会与他合作。”
这一趟来沪,于佩尔的儿女同行。马可·穆勒特意号召上海电影学院的师生们给于佩尔的大儿子洛伦佐鼓掌。巴黎当地时间4月9日,邵艺辉导演作品《好东西》在法国公映,“为影片做法国发行的正是洛伦佐,此前他和他的父亲还一起张罗了30场提前点映”。
一位意大利电影人、一位法国女演员、一群中国青年人,在上海交换了关于艺术的认知,也惊喜发现——原来许多问题,我们的理解、困惑与向往,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