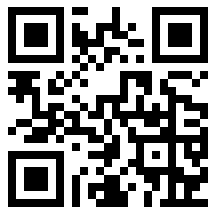在生死时速的竞技场上,一道自动门将人间悲喜切割成两个世界:门外是攥着检查单来回踱步的家属,门内是连呼吸都需要仪器代劳的生命。这道门,或许是现代医院最具哲学意味的存在。它既是一道物理屏障,隔绝着生与死的焦灼;也是一面精神棱镜,折射出人性最深处的光与影。

在这道门内,时间以监护仪的心跳频率丈量,这里的对话常被呼吸机的警报声打断,而这里的医生,每天都要在希望与绝望的钢丝绳上完成高难度平衡术。
15年间,青岛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ICU医生薛翠亲手推开过这扇“生死之门”几千次,见证过垂危生命迸发的惊人意志,也经历过回天乏术的至暗时刻。在无数次与死神的谈判中她也有所参悟:比挽留生命更重要的,ICU教会人们如何与生命和解。

薛翠
这里是生死交锋的战场
4月18日下午1点多,青岛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ICU病房外的排椅上坐满了病人家属,他们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扇门上,门里面是需要监护的重症病人。相比于其他病房的门,那扇门显得格外沉重,多数情况下它是紧闭的。

正值医生与家属沟通的时间,已提前在手机上与病患家属约好的ICU病房医生薛翠走了出来,并排坐着的五六个家属立马起身,快步来到薛翠面前,“医生,我的家人怎么样了”“呼吸正常吗”……他们声音急促,接连抛出几个问题。
“病情还没脱离危险期,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想带他去做CT,呼吸机都准备好了,但是他现在还不具备被移动的条件。”薛翠把病人的病情、可能出现的情况,向家属们一一罗列,治疗方案有几种选择也一并与家属沟通。
就在当天上午,薛翠给部门医生培训时,还着重强调了跟病患家属沟通的重要性:你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但其实你面对的这个病人所在的一个家庭。
“这里的病人情况都很严重,有时病情突变,家属往往难以接受,情绪难以平复,这时,医生与家属的沟通非常重要,一定要将心比心。”薛翠说。
ICU医生的角色从来不只是“救火队员”。站在医学与人文的交汇点,他们眼中盯着呼吸机参数,手中托起家庭命运的砝码。薛翠在强调“一个病人背后是一个家庭”时,她道破了现代医疗体系中最易被忽视的真相:那些监护仪上的曲线,实则是无数个家庭的情感心电图。


“作为医生,我们可能在情感上帮不上太多忙,但可以递上一张纸巾,倾听他们,安慰他们。”沟通不仅限于解释病情和情感慰藉,最主要的是与家属一起商讨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尊重家属的决定。这涉及到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家属对病情的理解力,还有期望值等多重因素,需要医生综合考虑,尽量平衡医疗需求与家属意愿。
ICU,是英文“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意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是医院中专门收治危重患者的科室。在这个地方,生命和死亡每天都在交锋,医生、护士与疾病展开一场场较量。ICU医生的职责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维持生命”。
在这里,医护人员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治疗方案,稳定危重患者的生命体征,尽可能恢复器官功能,并争取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面对疾病,我们和患者是盟友。”薛翠郑重地说。
毋庸置疑,ICU病房就是现实世界里生死交锋的战场,医生是整个战场的指挥者,承担着高强度、高风险、高技术的工作任务。
“在ICU工作,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因为常常面对死亡,得做出调整,不能因为一位病床的病人不好了,就在这儿跟着难过,还有其他的病人等着你呢。”薛翠在劝导年轻医生时如是说道。

薛翠给年轻医生讲课的笔记
“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得学习,都得了解,患者的病情演变发展、危重情况可能到什么程度,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薛翠说,一名ICU医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快速做出反应的能力。
“比如进来一位昏迷的病人,要快速判断昏迷的情况,从外科到内科,像一个树杈一样,一级一级慢慢顺下来摸清楚。”这个过程需要医生思路清晰,判断迅速,果断拿出有针对性的抢救方案。
“ICU相当于一个桥梁。”薛翠说,每天大量的工作是沟通多学科会诊,这常常需要兄弟科室来协助,“心跳呼吸骤停的病人,往往不是单纯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有可能是脑神经功能出现问题,也可能是肝功能、肾功能不好了,很多病情需要综合救治。”
“最开心的事是看到病人康复,会觉得自己太有成就感了。”作为ICU的医生,薛翠比任何科室的医生都希望看到一个人从昏迷到可以自主呼吸,再到可以坐起来、直至正常行走的全过程,“看到病人康复,我们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每个人的求生欲都很强
“我救治过最小的病人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15年的ICU工作,让薛翠经历过不知多少场与死神拉锯的“硬仗”。

刚参与ICU工作时,一个小女孩因为车祸右下肢粉碎性骨折,医护人员都很照顾孩子的情绪问题。她记得,“因为小朋友总是哭闹,我们有的充当姐姐,有的充当妈妈的角色,喂饭、哄睡,陪她玩。有个护士把橡胶手套吹成一个小气球,还在上面画上一个笑脸,逗她开心……”
“印象最深的、最惋惜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薛翠每每提起都会叹惋,他是服用了农药百草枯中毒被送来的。
“小伙子交了一个女朋友,妈妈反对,于是他跟妈妈赌气,喝口农药本来想吓唬一下妈妈。喝完农药后,他还跑到海边散心去了,晚上就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赶紧到医院洗胃处理,立马做了血液净化。”薛翠记得,小伙子刚送进来时,还在跟父母置气,说不想理父母,不见父母。第三天开始,他慢慢喘不上气来了,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
“他觉得抿了一小口农药,没事儿,因为我们平时喝一大口水至少50ml以上。”但是薛翠很清楚,百草枯喝上不到10ml都会致命,死亡率非常高。
“小伙子与父母见面时,妈妈哭他也哭。”薛翠很无奈,“后悔也没办法,真的没有给你后悔的机会。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不该跟父母赌气。”
这个病人一住进ICU就喊薛翠姐姐,在他弥留之际,意识清醒的时候还向薛翠倾诉:“姐姐我好想活着呀,我以后再也不吵架了,我再也不跟我爸妈赌气了……”
虽然薛翠和同事们穷尽了抢救手段,透析、插管、上呼吸机……但是小伙子还是慢慢变得神志不清,不到一周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经历生命最后一段路的人,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很想留在这个世上。”薛翠曾经抢救过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直到最后他的意识都是清醒的,疼痛让他在身上抓出了血痕,嘴里不断地念叨:“救救我……”
“哪怕是一个癌症病人,前期再怎么看得开,嚷嚷着:哎哟,我死了算了,已经没得治了,我不想遭这个罪了。但是到了生命最后一段路,就是另外的态度了。每个人都是向往生的,生命最后,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求生欲望。”薛翠说。
“还有一种情况,对医生来说比较无奈,就是评估这个病人还有抢救的机会,但是被家属错过了。”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有的是病人家属出于传统风俗观念,比如老人不能在外地去世,要送回农村老家;还有的是家人意见不统一,拿不定主意,耽误了。
每当这时候,薛翠都会劝一劝:医生真的很想再努力挽救一下。“但是如果病人家属执意要签下放弃治疗,也是很无奈。”
站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ICU有时如同一面放大镜,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面镜子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医生在此刻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执行者,而是生命叙事的重要见证人——他们记录着人在生死关头的悔恨、不甘与眷恋,也见证着亲情在绝境中的撕裂与坚守。
薛翠曾经救治过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到了生命后期开始呼吸衰竭——疾病在慢慢地消耗掉他的生命力。
虽然医生们都知道此时已经很难回天,但当老人进入抢救室的时候,家属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是插管维持生命,还是安安静静地送他走?
家属们非常犹豫,在门口商量了很久,然后告诉薛翠:“医生,请你们插管。因为家里有孩子马上要结婚了,你让我们家里人怎么办?一边办喜事,一边办丧事吗?”
薛翠和同事们给老人插了管,在呼吸机的支持下,老人又醒了过来。
插管、依赖呼吸机的状态什么样呢?气管被切开,不能讲话,离不开呼吸机,活动范围只有那一张床。当并发症一次又一次来袭的时候,老人的状况越来越差,到最后他手脚紧缩,蜷缩在床上,像一截枯树桩。这种状态让薛翠这样常年从事ICU工作的医生看了也很不忍心。
经受几个月的折磨后,老人走了。面对这类抢救,薛翠心里是另一种无奈:有时候病人的医疗决策是由家人做的。面对死亡呈现的伦理困境,恰是现代医学进步的伴生难题。
“我有时会向病人家属做这样的比喻:当叶子必然要落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强留在枝头上吗?目送它自然飘落,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只羡慕那个健康的自己
在ICU这个各种仪器嘀嗒作响的空间里,医护人员是需要24小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15年ICU工作,薛翠的手机从来不关机,铃声调至最大音量,“有突发情况,我随时是需要赶到医院的。”
“网络上有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出现。珍惜生命,投入地过好每一天,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不能否认的是,ICU工作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薛翠的人生观。
很多进过ICU的病人告诉薛翠一句话:“我不羡慕有钱人,我只羡慕原来那个健康的自己。”对此,薛翠笑着回应:“很简单的例子,当你牙疼的时候,你才知道大口吃饭有多香。”
这种生活态度恰是对ICU生死课的最佳注解——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感知温度的能力。
生活里,薛翠是个很佛系的妈妈,今年41岁的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上五年级,小女儿上一年级,“从来没给孩子们报过额外的学习班,即使大女儿已经五年级了。”很多孩子的周末排满了语数英辅导课,而薛翠在每个周末都会带孩子们出去爬山散心。
“有句玩笑话叫:逼疯一个母亲只需要一个小学生。但是我觉得只要她开心就好,这是最重要的。”话虽如此,但有时候女儿考试成绩不理想,薛翠也会忍不住焦虑一下,偶尔“卷”一下,狠抓一段时间学习。
“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医生,经常值夜班。我们两个人有时都不在家,从时间上就不能做到时时监督孩子的学习。”薛翠无奈地说。
在薛翠眼中,“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少熬夜、少操心,跟周围的人平和相处,让疾病能够远离我们。”这就是她最简单的生活期许。
死亡并非彻底的失败,而是生命教育最后的教科书。当公众习惯用“奇迹”或“遗憾”定义ICU的故事时,无数医生用坚守和“平行病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医学人文精神,是在技术极限处依然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在无力回天时仍愿递上一张拭泪的纸巾。
这是一个ICU医生清醒而又温暖的凝视。
医生手记>>>
面对生命的陨落
从事重症医学科这么多年,本以为自己已经能用很平常的心态面对各种患者的死亡,但是,这例患者的死亡,再一次触动了我……
一个平常的夜班,像往常一样接班,刚巡视完病房,科室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护士一看急诊科的电话,和我对视了一下,一般这种情况,要么下去急会诊抢救患者,要么准备接收患者。电话那头通知:“急诊科正在抢救一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喝了三大口,正在洗胃,处置完收到ICU……”值班护士挂了电话边准备,边告诉我。
我脑海里闪出了念头,这都2021年了,2018年不是国家明确不允许生产百草枯了吗,怎么还有呀?不管是什么患者,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口服,多希望他(她)喝的百草枯是假药,或者是过期药……
没等我思虑太多,患者由急诊的医护人员陪同收到我科病房,我见到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几岁,叫他小杰吧。他面色红润,有说有笑,没有一点抢救指征,用医学术语形容就是“一般情况好”,而他现在躺在重症医学科病房里。
“你喝了多少?我们要根据你喝的多少,来计算用药量。”我问他。
他双手交叉放在枕后,轻松地回答:“我听说除草剂对人没毒,就喝了几口,差不多两三口吧,我没想着死,就想气一下我爸妈。”
他所说的除草剂是只要喝不到10ml就能致命的百草枯。护士边上心电监护边询问患者一般情况,小杰还不太配合,“我没什么不舒服,不是洗了胃了吗?不用给我监护,不用打针……”
我出去与患者爸妈沟通病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心里又急又燥。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百草枯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水溶性极好的化学剂,而人体体重的70%又恰恰是水。也就是说,人体对百草枯而言就像一块海绵。在相对缓慢的侵蚀过程中,患者的肺会逐渐纤维化,呼吸变得困难,即使医院给足氧气也无济于事。肺还不是百草枯唯一的靶器官,肝肾等脏器也是侵蚀的目标。可怕的是,百草枯对大脑中枢神经的损伤却不算明显,以至于在痛苦而又缓慢的死亡倒计时里,大多数情况下患者都意识清醒。这简直是比绝望更绝望的死法。
以当前的医疗手段,除非喝下的百草枯是假药、严重过期药,或摄入剂量极其轻微且送医及时,否则病患九死一生。目前百草枯中毒还没有很好的解药,能做的只是减轻痛苦,减慢病程,从死神那里争取时间,患者往往到头来人财两空。
跟患者家属解释后,我让他们尽快筹钱,为儿子多争取一点时间。
沟通完病情,立即着手给患者完善各项检查、建立股静脉通路紧急行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并给予暂禁食、胃肠减压、鼻饲白+黑(思密达+药用炭片)治疗方案,并给予镇痛镇静、护胃、抗氧化、激素、维持内环境等对症支持治疗。
小杰爸妈通过上网、找熟人等途径也打听到了这个病的预后极差,死亡率极高,每日沟通病情,他爸妈以泪洗面。
第二天,小杰说:“医生姐姐,我就是有点嘴巴疼……”
第三天,小杰说:“医生姐姐,我肚子有点不舒服,难受……”
第四天,小杰说:“姐,我什么都配合你,你早点治好我,我请你吃饭哈,其实我真的不想死。”我别过脸:“先治好了再说,好好配合就可以了……”
第五天、第六天,小杰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呼吸困难越来越重,肝肾功能越来越差,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
第七天,小杰呼吸衰竭、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神志昏迷,最终还是没能闯过最后一关。他走了。
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久了,见到了太多生离死别,也见到了太多人世间的无奈。感慨生命的伟大,也感慨生命的脆弱,一念之差,却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偿还。百草枯中毒,给你后悔的时间,却不给你后悔的机会。
医者仁心,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患者,不管患者的社会地位如何、家里经济条件怎样,最想救活他的永远是他的医生,有时候患者家人或许会因各种因素不再坚持治疗,但医生救治的心永远不变。
医生也有无奈,医学是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学科,医学不是万能的,但是医生会竭尽所能。
重症医学科 薛翠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高芳)